国内一些人对此感到吃惊,因为此前的欧洲议会选举以及欧洲多个国家的选举似乎都给人“右翼势力日渐强大”的印象,为何英国这次会“左转”呢?
实际原因十分复杂,甚至可以说“英国左转”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
上届英国大选(2019年),工党遭遇史无前例的惨败,仅赢得202个议席,但得票率却不低,为32.1%,仅比史无前例大胜的保守党(365个议席)少了11.5个百分点。本次大选,得票率其实只有38.7%,仅微涨了6.6个百分点,但保守党得票率却暴跌至29.5%,暴跌14.1个百分点。虽然一个只涨了一点点,一个却暴跌,相对差距拉大,前者自然获益。
保守党得票率暴跌的罪魁祸首是极右翼改革党:上次选举,改革党一个议席都没拿下(后来因为保守党议员叛逃而赢得一个议席),得票率仅为2.0%;此次,其得票率飙升至14.3%,直接拿下的议席增加到5个。可以说,中右翼的保守党向极右翼改革党丢掉了不少选票和议席。
英国独特的选举制度放大了极右翼的破坏效应。
英国采用“简单多数制”(FPTP)投票制,而非比例代表制(PR)或法国的两轮投票制,这意味着每个选区中得票最高的候选人即使得不到50%的选票也会当选。这种制度使得支持者众多、分散的小党派很难争取到席位,而支持者集中度低的小党派只能在自己的据点继承一两个席位,而仅有一两个席位在650个议席的下议院中没有发言权。即便是实力中等的政党也难以拥有足够的资源覆盖全部650个选区,结果就是国家变成了两大政党——一战前的保守党和自由党,一战后的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的对决,其他政党只能打酱油。
如果改革党和绿党采用比例代表制,那么根据得票率,他们在每次选举中的议席数都会达到两位数。但在上届选举中,这两个党派一个只获得1席(绿党独领风骚),另一个只获得0.5席(他们转投保守党,只获得1席)。

在很多右翼略占优势的选区,保守党和改革党候选人互相“抢风头”,导致在FPTP规则下被工党或其他党派候选人占了便宜。事实上,如果不是改革党候选人抢走了大量选票,右翼一般会获胜。在最早计票的两个选区,改革党候选人排在第二位,将保守党候选人挤到了第三位。如果是法国的选举制度(虽然是单选区制,但候选人必须获得半数以上选票才能直接当选,否则将在前三轮投票后7天重新当选),可能会在第二轮出现“弃选”(排名第三的候选人退出选举,支持第二名反对第一名),从而改变局面。 如果是PR选举制,保守党靠“党票”还能赢得一些议席,但FPTP“赢者通吃”,在中左翼工党占优、右翼“两匹马争位”的情况下,由于两位右翼党派候选人的争斗,导致右翼选票被分流,很多议席因此丢掉。
当然,把保守党惨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选举制度和极右翼的破坏,未免有些不公平:就连现在不少保守党政客也承认,英国民众普遍担心经济衰退、社会保障恶化、非法移民、国民保健服务(NHS)排队时间过长,以及长期执政的保守党丑闻频发、政治上严重不信任。尤其是对近一年多来连续两次“私改”首相感到厌倦,形成了“只要不是保守党,谁都行”的普遍观念。事实上,除了保守党和苏格兰民族党2024管家婆开奖结果,大部分左、中、右翼政党的议席都有明显增加。 比如极右翼改革党议席从选前的1席增加到5席,中间派自由民主党议席从选前的15席增加到71席,绿党议席从1席增加到4席……显然,很多选民并没有“左转”,只是单纯地对保守党继续执政投了不信任票。只不过,FPTP选举制度的放大,让工党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因为这个选举制度的特点就是“赢者通吃”,而其他党派的左、中、右候选人只起到了转移保守党候选人选票的作用,只起到了“拆房子”的作用,也就是让保守党失去执政地位,而对于“建新房子”也就是重新组阁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还需指出的是,欧洲近年来的动向主要是极右翼的崛起,这与冷战结束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以自由市场和“新保守主义”为特征的中右翼垄断执政权不同。在很多国家,中右翼势力也出现“暴跌”。比如在刚刚完成国民议会首轮投票的法国,传统中右翼政党法国共和党在法国国民议会中以577席的总票数(在所有选举力量中并列第五)只直接获得一席,以64席(排名第四)挤进第二轮选举。这个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最多总统(4任)的“戴高乐派”传统中右翼政党几乎跌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真正崛起的是极右翼的国民阵线。 在德国和意大利,正在崛起的德国选择党、意大利兄弟党和五星联盟均为极右翼政党。作为上述国家传统的中右翼主要政党,前者的联盟党已成为反对党,后者现存最老大党意大利共和党多年来在“三院(意大利参众两院和欧洲议会)”中议席为零。
对应欧洲大陆的英国极右翼政党是前面提到的改革党,前身是脱欧党,极端反欧、强调孤立主义、极端反移民,其“光谱”与欧洲大陆的极右翼政党十分相似,事实上近年来也在快速扩张,这次却没能收获多少,只能扮演“毁屋”的角色。 一方面,他们此前盲目追随美国极右翼和特朗普,甚至喊出“帮助特朗普上台比在英国投票更重要”的口号,引起众多同情者(欧洲极右翼传统上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拒绝“外交重于内政”的说法)的反感;另一方面,选前党魁陷入政治丑闻,多名重量级候选人被保守党挖角,导致大选准备不足,直到已退居二线的党内创始人奈杰尔·法拉奇)在危机时刻上任,果断放弃不得人心的极端亲特朗普“个性”,才终于稳住了地位。 简单来说,英国与欧洲大陆一样,近期也出现了极右翼势力明显崛起的现象,但由于保守党的“民愤”以及选举制度的影响,保守党“巨落”的遗产,更多地被原本是最大反对党的工党所瓜分。
事实上,欧洲不少国家近年来也因经济形势不佳,中左翼甚至极左翼势力有所崛起。以法国为例,法国左翼政党联合组成“新人民阵线”参选英国工党时隔 14 年再夺执政权,原执政党保守党惨败,背后原因令人惊讶,在首轮议会选举中获得27.99%的选票,明显好于上届的25.78%,仅次于国民阵线/特奥蒂共和联盟(33.15%)。首轮直接当选的76人中,左翼人士有32人,也仅次于国民阵线联盟的38人。进入第二轮投票的1306名候选人中,左翼人士有407人,仅次于国民阵线联盟(447人)。 坦白说,国内一些舆论对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的“战果”有些夸大:由于法国实行“前三轮决胜制”,许多左翼和中间派候选人为了阻击国民阵线,在第二轮选举中都选择“弃保潜逃”(即第三名候选人退出选举,全力支持第二名或第一名候选人与国民阵线候选人对峙)。国民阵线在7月7日第二轮投票后,很难独自赢得国民议会半数以上席位,通过跨党合作组阁更是难上加难,即便侥幸组阁,也会遭到重新崛起的左翼新人民阵线的强力阻击,即使在一定条件下,也不能排除组建左翼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即便将英国工党崛起简单解读为“左转”,英国也并非孤立无援。
此外,在上届大选惨败后,英国工党痛定思痛,以“温和派”斯塔默()取代了前“深左”领袖科尔宾,甚至不惜将后者开除出党。在“变革”的旗号下,斯塔默不惜抛弃工党长期以来推崇、他本人也一直认同的诸多传统左翼纲领,如高税收、高福利、国有化、大笔公共开支等,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必须齐头并进”,自称“亲商”,撤回了对加税、免除大学学费、大笔公共开支等政策的支持。他不顾党内多位元老的强烈反对,撤回了工党上台后每年投入350亿美元用于“绿色能源替代”的长期承诺,称“盲目扩大开支是不负责任的”。 他还毫不犹豫地剥去自己长期以来“反脱欧”的标签(这也是工党的一贯立场),并多次明确表示“英国没有理由重新加入欧盟”。
这些做法虽然招致了党内不少人“叛徒”的愤怒指责,但也吸引了大批对保守党失望、惧怕改革党、不认同工党传统政纲、执政后多次搞砸经济社会的中间派。不少分析人士指出,工党上一次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还是1997年,当时托尼·布莱尔靠“走中间路线,吸引摇摆选民”而成功,如今斯塔默不过是效仿而已。总之,此次英国左翼崛起固然有保守党“民愤”的外因,但也与斯塔默上任以来该党努力表现得“不那么左”息息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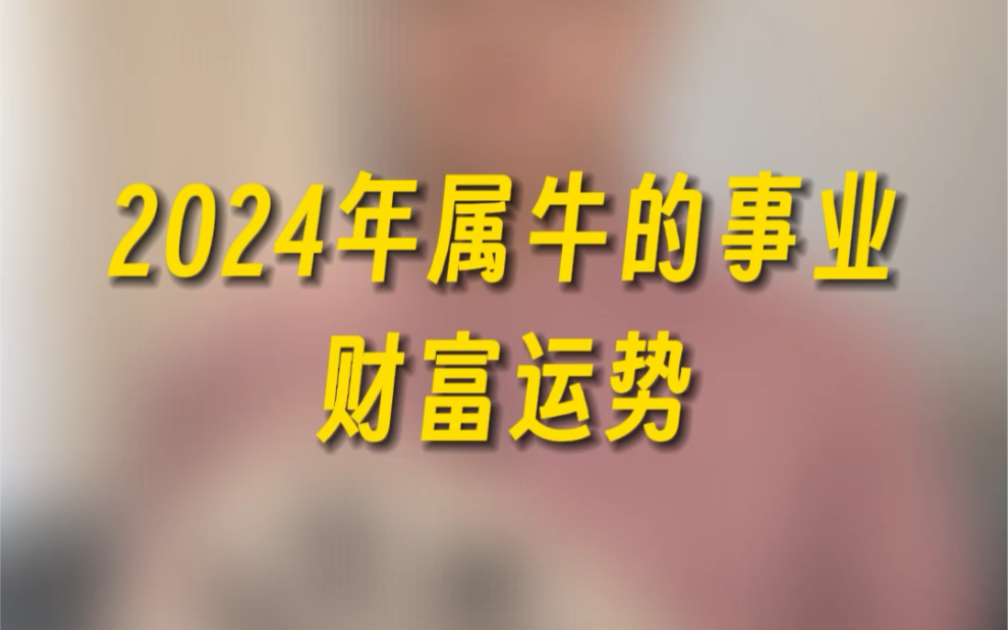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