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Ariel
编辑|庞莉
和妈妈、老公拥抱后,我一个人走进手术区,紧张、恐惧占据了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护士核对我的信息,问我的姓名、生日,我哭得哑口无言。护士撕下几张纸巾给我,又问了另一个问题,把我的姓名、生日念出来,问是否正确。我连连点头确认,护士就把我带进了手术室。
旁边是忙碌的医生和护士,护士扶着我爬上手术台,手术台太窄了,我担心自己笨手笨脚会侧身摔倒,于是小心翼翼地向右转,像虾米一样弯下腰。
“会有点疼,忍一下别动。”麻醉师扶着我的腰说道,“很快的。”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戳到了我的腰椎。麻醉师用力把它推了进去。我紧张地握着旁边护士的手。我身边的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工作。我握着的护士拍了拍我的手,让我放松。过了一会儿,我感觉脚趾麻木了。过了一会儿,我甚至感觉不到我的腿在哪里。
主治医生迎接了我,用绿色的手术布蒙住我的头,挡住我的视线。我在小红书上看到的那种在无影灯下看到自己肚子被切开的恐怖场景并没有发生。麻醉师坐在我头边,代替护士安慰我。
“我无法呼吸,而且感觉恶心。”我感觉好像身体里所有的力气都被抽干了。我只能用最简单的词语来表达我的感受。
“没事的,一开始你会不舒服,等会儿要是还不舒服,我就让你睡着了。”麻醉师把氧气移到我鼻子前面。
主任把我的肚子切开了,我什么感觉都没有,然后就感觉肚子被往下挤压,一阵急促,然后有些嘶哑的哭声,刚刚停住的泪水又流了下来。
“17点15分,7.3斤,男孩。”护士喊道。我心里默念了几遍,记住了时间。手术室里一下子轻松起来,主任一边缝合,一边随意地聊天。“你们都哭了,一出生就哭了,感动得眼泪都忍不住了。哎,长大了,也会有生气的时候。”
我也跟着哭了又笑了。护士把洗干净的宝宝抱到我脸上。他软软的,凉凉的,感觉既陌生又熟悉。
我认为,生育应该顺其自然,如果有了就坦然接受,没有了就不要勉强。
我的一个闺蜜在38岁时顺利生下二胎,她告诉我,现代人很注重保养,生育年龄也比较大,所以不用担心,先好好享受生活就好。如果担心,去检查一下生育能力,就知道了。
我把这句话牢记在心,并在三十多岁时一直摇摆不定,直到三年前我第一次意外怀孕。
发现两条线的那天早上,天还黑着呢。我的月经推迟了一周多,所以我早早起来去卫生间检查。果然,两条淡淡的线,若隐若现。我赶紧坐在马桶上,用手机看了看。原来,只要有两条线,不管深浅,都意味着怀孕了。
我赶紧回到床上,告诉也醒了的老公。他很平静,好像早就料到了一样。啊,怎么办?我还没准备好。我像小猫一样蜷缩在厚厚的被子里。老公看到我,笑了。这张宽大的床,让我看起来更可怜、更弱小、更无助。
该怎么办呢?我赶紧订购了《海蒂的怀孕百科全书》,立即开始阅读,用知识缓解焦虑。没看几页就给诊所打电话预约检查。护士说现在还太早,只能抽血检查。结果和验孕棒测试没什么区别,最好等到第六周再做B超。护士细心地帮我计算B超检查的时间。我渐渐接受了事实,放下紧张,收拾行李。转眼间一天就过去了。我收拾行李准备和兴奋的老公出去吃羊肉火锅庆祝一下。
很快就到了做B超的日子,我们不想让父母提前知道,就找借口去医院检查。3*3mm,比绿豆还小,但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赶紧去了两个月子中心才回家。我们很开心,但又不好意思跟父母说,我们想等到10周再做基因检测,比较稳妥再说。可老公却忍不住时不时摸摸我的肚子,开心极了。
但过了一周,我开始有褐色出血。我问了生过两个宝宝的闺蜜,她想了想说这好像很正常,有的人会有这种经历。又过了一天,我又有鲜红色的血,于是赶紧去医院急救,爬上床,让医生做内检和B超。出血已经止住了,但没有胎心。
我在前台等着拿报告的时候,前面排了一对年轻夫妇,脸色阴沉。值班医生告诉他们希望不大,让他们再考虑一下。然后他看了看我的报告,抬头对我说:“再等一会儿,再去验血。虽然不确定,但还是有机会的。”
老公帮我预约了,验血结果也同步发到他手机上,他在网上查结果,越看越难过,但他不敢告诉我,只是安慰我。
两天后我又去验血,检查HCG值翻倍了。只要HCG值正常增加,就说明胚胎发育正常。但结果显示HCG值偏低。医生又做了更详细的B超检查,一个人检查完后,第二个人又看了一眼,让我躺在另一台机器上。
“这两台机器有什么不同吗?”
“这个机器是专门用来检测畸形的,看得更清楚。”
还是听不到胎心,医生检查了里里外外,然后跟我解释道:“我们需要看看是不是其他地方的宫外孕。”但我的心沉了下去,没有希望了。
两天后,我胃里翻腾,疼得浑身冒汗。疼过后,我想洗澡。洗澡时,我感觉有温热的东西顺着腿往下滑。我低头一看,发现一块不到手掌大小的肉,红白相间,像五花肉。我按照医生事先的嘱咐,赶紧把它装进盒子里,穿上衣服,冲向医院。
第二天就是我要住院做药流的日子了,还有很多东西要准备,不过现在倒是省去了不少麻烦。
医生没说是什么原因,只是说流产是正常的,四分之一的女性都会经历流产,可能是胚胎的优胜劣汰,也可能是身体还没有准备好。
“没事的,别难过,别后悔,还会有明天的。”我们去看了一位著名的老妇产科医生,她快70岁了,慈祥得像个奶奶,笑眯眯地给我们开导。
过了半年,我们以为又要准备怀孕了。很快,两杠又来了。这次我不敢掉以轻心。从发现的那一刻起,我就赶紧预约了验血,每三天去抽一次血,HCG值翻倍,很正常,比上次高了很多。我们又期盼起来,算好时间,赶紧去做了B超,还是没有胎心。
“十天后再来。”医生说。十天过去了,还是没有胎心。躺在超声检查室里,我的腿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医生给了我一张转诊信,让我去医院安排药物流产。
怎么了?我问了老医生,她只说自然流产三次以上才算是习惯性流产,有些流产是概率问题,所以还是再试一次吧。
我不相信,在等待医院安排入院的这段时间,我开始订购各种不孕不育方面的书籍,比如《怀孕生子》、《你的身体适合怀孕吗?》,也开始在小红书上搜索类似的经历。我不能第三次这么被动,我的身体和孩子都不是实验对象,我不能一直尝试下去。
那段时间,丈夫每周都请假陪我做检查,他跟老板说:“我老婆可能需要做手术。”由于当时工作不是很忙,老板也非常理解和包容。
每次我们都坐在候诊室里,眼神焦急。每次医生都会保守地让我一周又一周地检查,让胚胎有足够的时间发育,希望它只是发育缓慢,或者怀孕时间计算不正确。但每次都没有新的变化,我们不再抱有希望。直到第十周,真的不可能了,医生才安排我住院做药流。
流产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母体缺陷,一种是胎儿缺陷。解决的办法是采用排除法。
在医院服药后,我强烈要求做胚胎染色体检测。但香港政府医院只对流产三次以上的人做胚胎染色体检测。从怀孕到每次检测后的失望,整整一个月我都没有流过一滴泪。当护士拒绝我时,积攒已久的情绪爆发,我泪流满面。“这是第二次了,情况一模一样,我和老公都做过检测,没有问题,就是想知道原因,难道我自己付钱不行吗?”两个护士哄着我。过了一会儿,护士长过来告诉我,她特意申请,帮我安排检测。然后签了一沓授权书。我感激不尽。
但两周后,检测中心打电话给我,说样本太少。可能是胚胎太小或不完整。无论如何,提取没有成功。我仍然不知道流产的确切原因。至于费用,免了。
确实是不完全,药流后复查发现子宫里还有一块残留物,继续吃药,每周去医院复查,如果流产物不能取出来,就得做手术刮宫了。
这次的“宝宝”比上一次好多了,是想努力留下来吗?按周数算,应该有蓝莓那么大,但还没过心跳,还比芝麻大一点。我还没能感同身受地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但它好像懂事了。两周后,它默默地消失了,让我免于更大的伤害。
第二次流产后的几个月里,我一边休息,一边研究各种流产治疗方法。有的测激素周期,注重自然调节,有的用中药,有的用第三代试管筛查基因。但无论哪种方法,都属于“生殖医学”。
原来,我之前看过的妇产科医生,都是处理成功怀孕和各类分娩的,如果情况不顺利,他们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尝试。
我的一个“算命”朋友在给我算命,算命的时候,她对我说:“你要小心保胎,你这个命盘不容易怀孕。”我听后很惊讶,我流产两次的事情,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怎么可能一句话就告诉她?
“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你命中注定会生儿子。”那位“算命”朋友安慰我,告诉我要向贵人、中西医、祈祷神灵等寻求庇护。
在老公老家探亲的时候,我们在紧凑的行程中特意安排了一天去五台山,深秋的阳光暖暖的照在身上,到了五爷庙的时候,我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也许是和暗夜里的神灵产生了共鸣,也许是想到了之前两次的失败,哭过之后心里轻松了许多,仿佛心里又多了一些信心,重新开始了备孕的旅程。
回港后,我找到一位据说帮不少港星生过孩子的医生,把前两次流产的时间、星期、检查结果列成一份详细的表格,和老公一起去看医生。
在奢侈品商店林立的海港城,有一栋写字楼几乎全部被私人诊所占据。他们能在最便利的地段支付最贵的租金,间接证明了医生的医术之高。我在小红书上搜索,找到一个和我有同样经历的姐妹推荐了这家名医,我提前一个月就预约了。
这是一位身材瘦小、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男医生。他的诊所外贴满了他在报纸上发表的专栏文章和综艺节目里的科普片段,还有襁褓中的新生儿照片,其中很多都是双胞胎。走进医生的办公室,架子上摆满了各种感谢卡和各种婴儿小玩意。
他听完我们的描述,简明扼要地帮我们分析了可能出现的情况——可能是妈妈的问题,可能是爸爸的问题,也可能是胚胎的问题,都是我在书上看到的原因分析。然后安排了检查。不到十五分钟,我们就完成了问诊,然后去找护士抽了12管血。两周后我们就能等到结果了。
“先生,绝对没有问题,至于你,基因检测显示有两个小问题,简单来说,你的血液太稠了,无法给这么小的胚胎供血,没有养分,胚胎就会饿死。解决办法也很简单,从备孕开始,每天吃阿司匹林,怀孕之后,你会开始打两针,我们称之为‘稀血针’,它们会让你的血液不那么稠,一针每月打一针,另一针每天打一针,不难。”
原来是免疫凝血问题。医生用最简单的比喻给我们讲解,但流产的原因却非常复杂,甚至违反直觉。按照传统理论,孕妇要远离活血化瘀类药物。《甄嬛传》中的堕胎神药麝香,就是险些抹去后宫中胎儿的活血药。但在现代科学中,像我这样的情况,整个孕期都需要服用药物稀释血液,分娩前停用,避免大出血。
这是医学界在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认识和治疗的一个“病症”,其应用和治疗甚至晚于体外受精。在阅读学习过程中,我了解到,这一治疗方案刚应用时,很多产科医生甚至不敢用药物。
但那位带着金丝眼镜的医生讲话很轻松,不到十五分钟,我们就结束了这场每次收费1500元的会诊。
大致找到原因后,我们就赶紧买房装修,筹备因为疫情推迟了一年多的婚礼,等到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已经过去一年了,又重新扛起了备孕的任务。
如今疫情已结束,香港与内地的边境口岸也已恢复。不知为何,我隐隐有种想重新审视流产原因的念头。会不会有其他原因?要不要多听几位医生的意见,以免遗漏任何细节?下次怀孕,我要确保只成功不失败。
我又开始了漫长的求医之路,每次看病都要抽十几管血,几趟下来,我的血洒遍了珠三角。
从距离香港最近的城市深圳出发,我选择了一家科研和服务都备受好评的全新三甲医院的生殖科主任,他是从市妇幼保健院挖来的副主任,在小红书上的评价也不错。
主任举止优雅,端坐着,昂着头,头发一丝不苟地卷成小卷,看了一眼我在香港做的英文报告,推给身边两个年轻的实习医生,年轻的医生们赶紧打开浏览器,开始搜索这些检查指标的含义。
原来,关于医生现场检查的笑话是真的。我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只要年轻医生检查,我就等着。然而,慌乱的年轻医生显然没有找到正确答案,因为香港发来的报告是基因检测报告,而不是内地常见的血象指标报告。
“再检查一下,我觉得不是凝血,要是凝血的话,胎儿也不会停那么早,连胎心都没有。”不等年轻医生们去百度搜,主任就给我下了结论,并给我开出了一沓验血单。
“还有你老公,有点胖吧?坐着都挺有肚子。”导演看了一眼旁边坐着的老公,刚陪她玩的老公赶紧坐直了身子,收紧肚子,不满的说,“我天天健身,肌肉发达才胖的。”
我们有些沮丧地离开了医院。一周后,我们在手机上收到了另一份检查报告。虽然结果并非全部正常,但我们没有去找主任进行复诊。
之前买的《怀孕生子》这本书的作者在华南最大的私立生殖医院工作,在公立医院预约专家非常困难,但在这里只要付费就可以预约。我本身是生育能力强的体质,但我们备孕的第一个月又一次怀孕失败了。发现当天我们就开车去了广州,预约了这本书的作者和省生殖领域的专家。
等待检查结果的时候,我一边看墙上的医院介绍和科普,医院开业以来,接诊了几百对夫妇,顺利生下百余个孩子。我心里暗自盘算,出生率还不到三分之一,不禁开始担心,这次的保胎能不能成功。
老教授年逾七十,一脸愁眉苦脸,身边还跟着两个像保镖一样的年轻医生,眯着眼睛看了看我从香港和深圳拿来的报告,战战兢兢地写出一沓验血单,写上一串蝌蚪字,推到我面前,让我付钱买药,整个过程他一句话也没说。
我拿着处方,一一查看这些药物的说明书。泼尼松、环孢素、环磷酰胺……这些都是治疗白血病和器官移植的强效药物,用于抑制免疫系统,防止免疫系统误将胚胎当成异物攻击,导致流产。我有那么严重吗?有那么严重吗?
想到自己花了上千块钱看门诊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心里不禁有些气愤。我回到教授办公室想问个清楚。老教授摆摆手,让左右护卫给我解释,却被我一句话噎住了:“说了你也不会明白。”
我气得连药都没拿就走了,可能是太生气了,也可能是怀孕激素的作用,出了医院坐在车里眼泪就流下来了。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连解释都解释不清楚?想到香港医生用最通俗最朴实的语言跟我解释,在广州却受到这样的对待,我委屈得哭个不停,不知道这次怀孕会走到哪里去。老公把车停在路边,摸摸我的头安慰我说我们只是尽力了,广州的医生确实不太好,他也觉得太过分了,但是我们还有其他医生可以选择的,对吧?
但保胎任务紧迫,每一天都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必须在胚胎停止发育前找到解决办法,不想再失败。
老公开着车,载着我和看不见摸不着的宝宝,穿越广袤的珠三角大地。珠江就像一张纵横交错的渔网,把各个城市分割成一座座水乡。经过一座又一座的桥,仿佛在告诉人们,只要我们找到路,路就永远畅通无阻。
经过一圈的奔波,我们回到珠海,找到了离父母家最近的一家三级医院,这是老教授任职的医学院校系统的另一家附属医院。我带着在香港、深圳、广州积累的越来越厚的检查报告,再次约见了复发性流产科主任。
“教授开的药你不敢用吧?”操着北方口音的主任看了我在广州的门诊记录后笑着说,“他开的药都很强,还给你开了很多免疫球蛋白G,这个免疫球蛋白老王子给大家开的都是这个药。”看来他很了解老教授的作风。
“我看你的免疫和凝血检查结果确实不是很典型的问题,如果不是以前有两次不良流产史,我想你是不需要治疗的。但在香港做的基因检测显示你确实有这方面的隐患,那我就按照香港医生的治疗方案给你开药,你一个星期来两次HCG和B超,正常情况下不需要检查那么频繁,但你不同,我们坚持检查,直到HCG上升到十万以上,检测到胎心我们就放心了。”
主任就像一位老太太,耐心地给我详细讲解,花白的头发随意地扎成马尾。最后一位内地医生看懂了香港的检查报告,没有让我再抽12管血。我的心也得到了安慰和平静。
终于打完针,老公就带我去金台寺祈福。那天是佛教节日,金台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我们穿过长长的山门,来到清水环绕的山脚下,手牵手顺着山坡往上走。沿途樟树盛开,清新幽静。到了山顶主殿,气势磅礴,我们恭敬地接香许愿,虽然心里还是有些紧张,但心情好了许多。
在到处求医的过程中,我偶然加入了其中一位医生的病友群。
虽然我们被称为“患者”,但其实我们都是健康正常的人,有的是上班族,有的是自己做生意,共同点是都经历过各种流产问题,我们互称姐妹,生完孩子后就成了阿姨。
流产是一件不宜与他人分享的隐私事,但也是一件难以独自平静的悲伤事。
在群里,因为有着共同的痛苦,我们毫不犹豫地讲起这些“病史”。有的姐妹即将临产,但肚子里的孩子却没有心跳;有的姐妹第一胎顺利,第二胎却屡屡失败;有的姐妹卵巢早衰,取不到可用的卵子;有的姐妹在等待试管,准备期间吃了不少药……
流产问题千差万别,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在通过反复试验寻找答案。我们不是孤立的案例,我们并不孤单。
不说各自的“病”时,我们在群里聊着各种话题,从每次体检结果的分析,到备孕育儿产品的选择,从下午点云悦咖啡,到生完宝宝后炫耀。共同的伤痛,成为我们互相扶持的绷带。
也是在流产之后,我才意识到生孩子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容易。
我和几个朋友吃饭,发现每个家庭都有过流产的经历,有的甚至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不得不辞职休养。我和同行们聊了聊,发现很多孩子都是通过试管婴儿怀上的,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甚至很多公司的商业医疗保险都把试管婴儿纳入了报销范围,下一步就是把冻卵也纳入。
有句笑话说,教育程度低的母亲生育孩子的风险较高,而教育程度高的母亲生育孩子的风险则较高。
在平均结婚年龄30岁、平均生育年龄35岁的香港,我很难说生育率低是不愿意还是不能。就连拥有各种医疗资源、费用不成问题的明星,也不避讳公开表达想要生孩子的痛苦。比如张智霖和袁咏仪不生二胎的原因,就是因为卵子老化。周润发夫妇、张卫健夫妇,都曾在孕晚期出现过胎儿死胎的情况。等他们熬过痛苦,已经来不及了,再也无法生孩子了。
我每两天去诊所抽血做 HCG 测试,看看指数翻倍的速度是否足够快,这代表胚胎是否成功植入。我还每周进行超声波检查,看看胚胎是否以每天 1 毫米的速度生长。
终于,到了第七周,躺在B超检查床上,我听到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急促而有节奏的“砰砰”声,这是我之前两次期盼的胎心声。
“哦系统探讨(管家婆一肖资料大全)两次流产后,我生孩子前注射了 250 次疫苗 | 三明治,那太好了,我也为你感到高兴。”院长看到我的报告后如释重负地对我说。很快,我就收到医院官方微信的推送,医院将设立生殖医学专科中心,专门应对日益严重的不孕不育和流产问题。
我也加入了“肝素宝宝”的队伍,每天晚上洗漱完毕,丈夫就从冰箱里拿出一针低分子肝素针,熟练地拔出针头套,在我手臂上找个没有淤青的地方,粗暴地插入,伴随着我痛苦的龇牙咧嘴。
针扎进去不疼,但当药物慢慢注射进肌肉时,整个肌肉都在抽搐,很疼。打完针轮流冷敷、热敷,第二天又重复同样的循环,直到产后一周打最后一针。总共打了250多针。每天早餐时还要吃阿司匹林,混着一堆孕妇维生素、钙片,全部吞下去。药物说明书上说,低分子肝素钠是用来治疗心肌梗塞、心绞痛的,而阿司匹林是常用的止痛、退烧药,还能预防心脏病、中风。
难怪二三十年前的产科医生都难以理解这些药物的用途。偶尔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我回到父母家,请退休的医生邻居帮我打针,她也说没听说过。“我们那个年代,孕妇是绝对不能用阿司匹林的。”她一头雾水,突然用针扎了我一下。“我儿媳妇怀二胎的时候,也打了很多针促排卵,我还以为你也是其中之一呢。”邻居带着孙子来我家打针,还跟我聊天,“现在的人为什么怀孕这么难?”
老公连续两次问医生,这个针是不是要一直打到分娩,医生说,不能说停针就一定不行,但是停针的风险是我们谁都不愿意冒的,对吧?
确实,只是打一针,疼痛感跟流产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如果不敢打腹部,可以打臀肌,或者手臂。肌肉注射随便哪个部位都可以,而且可以经常换注射部位,医生建议道。
除了打点滴,在最关键的孕早期,我们还是使用了自费的“赫尔墨斯”——免疫球蛋白G及其替代脂肪乳。既然要保护胎儿,我们能做的就都做了。理论上,这两种药能有效提高免疫力,避免我的免疫系统误以为胚胎是入侵的异物而攻击。据说免疫异常往往会导致凝血问题,而从研究数据来看,使用这两种药确实可以降低早期流产率。
先是住院注射免疫球蛋白G,医生开的十单位的处方,就是十小瓶点滴,每瓶680元,每半小时输一瓶,我按铃叫护士换药,等十瓶打完,我整条胳膊都凉了。后来换成脂肪乳,一小袋像牛奶一样的浓稠液体,比牛奶贵多了,一袋三千多元。慢慢地往胳膊里注射,我放下袖子盖上创可贴,又回去上班了。这本是平凡的一天,不同之处在于我每个月都算了一笔账,每月第一个客户带来的收入,全部用来养家糊口了。
我们整个孕期花了十几万来保胎,老公公司的商业医保有IVF,但是我们治疗的费用不比IVF低,因为时间太新,看上去是正常的产前检查,但是开的药很贵,还没有纳入报销范围,所以只能按照常规产前检查报销,保险公司还打电话问医生澳门2023年精准资料大全,正常的产前检查为什么开这么贵的药。
我的情况并非个例,在一群备孕的姐妹群里,我了解到在内地,所有辅助生殖项目,无论是免疫球蛋白G还是进口低分子肝素注射液,都是自费项目(直到2023年底,北京市卫健委才宣布,包括试管技术在内的16个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北京医保)。群里大家戏称自己的“女儿”、“宝贝儿子”,也确实名副其实。每一个没受过苦的妈妈,孕肚都比不上一个爱马仕包包。
但孩子的到来,并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我和老公不惜一切代价迎接孩子的到来,就像备孕群里遇到的那些准妈妈一样,她们说怀孕很花钱,但同时又安慰自己,“好不容易怀上,钱又算什么?”
幸好除了最初的挫折,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宝宝的各项检查都顺利通过。在这一系列的医生中,我们选择了香港和珠海最贴心的医生来负责产前检查和分娩。
或许是因为宝宝来之不易,被视为“宝贝”,再加上我和善良、技术精湛的医生们之间的缘分,在之后的治疗过程中,虽然每天都要打针,但我并不觉得分娩是必须忍受的痛苦,而是一种被呵护的享受。
十周左右产检时刚看到宝宝的样子,香港的医生就开玩笑说宝宝现在在私人泳池里很舒服;后来肚子大了再产检,珠海的医生就搂着我的脖子,帮我做完产检后站起来;临产前,我可以决定是顺产还是剖腹产。生产时,优秀的止痛技术和陪同的月嫂帮我缓解了除产奶以外的所有疼痛。一点一滴都让我很享受怀孕的过程,甚至觉得我还可以再生一个孩子。
回想自己准备怀孕的时候,曾和朋友讨论为什么要生孩子,是否值得彻底打乱自己和伴侣的生活方式,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养一个“神兽”,等它出生后还要对其负责到底。
是啊,何必呢,尤其是像我这样已经走到这一步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真正让我感动的是身边的父母们,他们虽然抱怨自己很累,但看到宝宝们的笑容,他们的心都融化了。通过孩子的经历和眼睛,父母们再次感受到了这个美好的世界,一切都是值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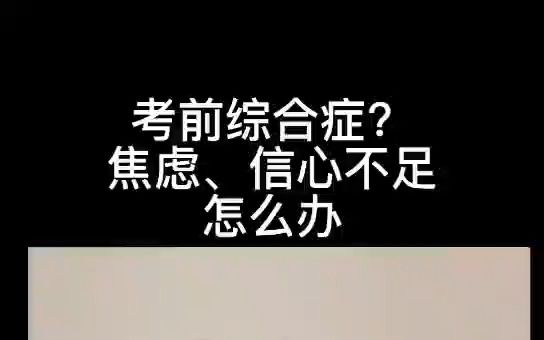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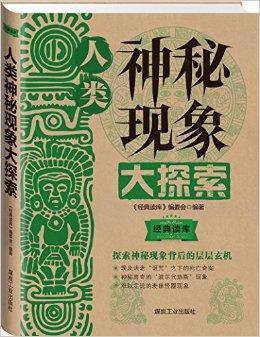






发表评论